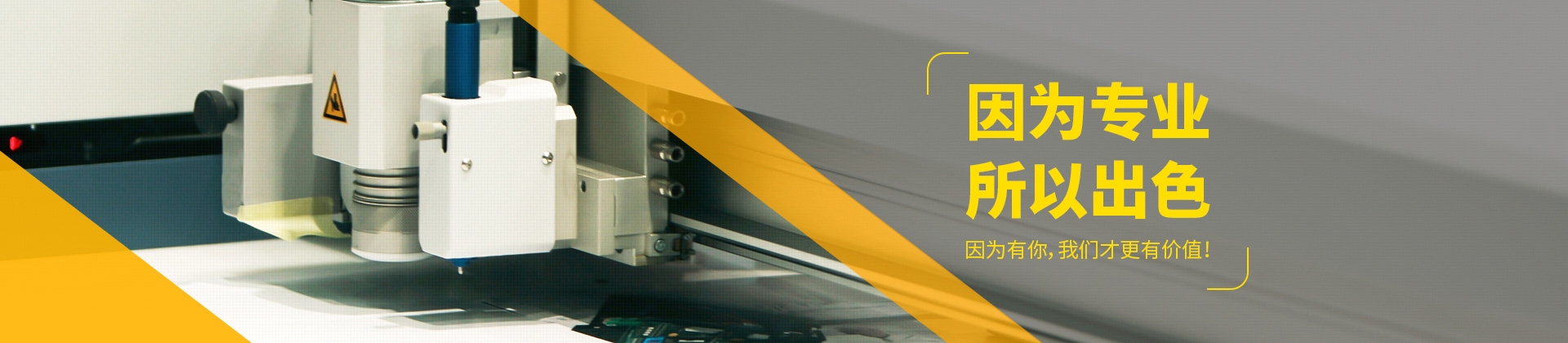主持人好,各位同事、朋友们好!谢谢主持人的介绍,很荣幸,在我们大成刑辩群这一专业的平台上,给我一个与大家交流的机会,向本次活动的组织者们道声辛苦,谢谢你们!也要特别谢谢在线的大成同事们,你们利用宝贵又温馨的周末时间,在线听同行的老生常谈,确实很难得,为表达对你们奉献时间的敬意,结束后我会给你们发红包,以示感谢。
这是我们大成律师事务所内的交流场所,业务方面,畅所欲言,工作方法,仁者见仁,俗话说“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杀鸡杀鱼,各有各的杀法”。鉴于此,今天我把自己的工作习惯、工作理念、工作方法如实地向大家作以汇报,以期对部分朋友有所启发,更希望借此获得批评指正、指点迷津,促进自我提升。
我所说的“二五三辩护”,实质上就是我做刑事辩护时对一个案件在公检法三区块的关注程度和精力分配。这是我自己的工作习惯,同行未必能予以认可,但我本人却因这样的工作习惯和方法,受益不少,辩护效果还是可以的。
我今天统计了一下本年度承办的案件,已经结案的十件案件中,四个判处实刑(其中三个案件是明显从轻判处,一个正常判罚),两个宣告缓刑,四个不起诉或撤案。开过庭未宣判的五件,二审两件,一审三件,这五件案子结果虽还没出来,但我感觉,我相信,或改判、或发回重审,或罪名不成立、或建议检察院的撤诉的案件还会出现,有极大几率会出现一到两例。我有信心会是这样的结果,若有好结果后我会在群里对大家说,当然,不是这结果我也安然处之,因为我尽力了。
这样不错的辩护效果肯定与特定的案件有关联,多是所谓的普通案件、小案件,要是办理案这样的案子,再怎么着也不会效果明显。但毕竟,我们做律师的,通过个人尽心竭力的辩护努力,对好结果的出现肯定会起到促成作用。
为了能尽可能把我想表达的内容表达清楚,借鉴韩友谊博士上周六在三亚大成刑事专业宣讲会上的发言内容,即:要进行充分有效的沟通,需要有共同的大前提,不然各自按各自的逻辑,永远说不到一起,说服不了,也说不明白。所以,谈我所谓的“二五三辩护”,我们也有必要先确定几个大前题,这几个前题是,一个假定、两个现实、三个认同。
假定我所讨论案件的模板是普通的一审案件,由公安侦查,具备正常的程序,律师在第一时间介入,历经逮捕前刑拘侦查、提请逮捕、批准逮捕、逮捕后羁押侦查,移送审核检查起诉、退回补充侦查、起诉至法院、开庭、庭后评审合议、宣判等所有程序。就是一般普通刑案,不是大案、要案、督办案、政治案,也不是案件的某一阶段。
应该说我们律师特别是刑事律师的专业化程度是比较低的,就全国律师群体来计,只做刑事案件的律师估计连1%也不到。我们大成在刑事专业化方面做得好一些,但也有相当长的路要走,比如大成刑委会入会条件也仅仅是“专门或者经常从事刑事法律业务的”。我们大家都知道,“经常从事”与“主要是做”不同,两者有一定的距离,而“主要是做”与“专门从事”刑事业务也不同。当然,“专门从事”还不够,“专门”和“专业”是不同的概念,“专门”侧重于量,“多办案多挣”,有点像走量的批发,“专业”侧重于质,“少办案办精”,有点像个人定制的精品。我们不仅要分清“专门”和“专业”的区别,还要觉察“平台魅力”和“个体能力”的不同。比如我们自己,可能会因大成的品牌、规模和业内合作,而案源多多、财源滚滚,但个人业务能力真的很高了吗,若离开外在平台,又将如何呢?所以说,“专门从事”与“专业敬业”,“平台魅力”与“自身能力”,是两码事儿,不要混为一谈,乱花迷了自己的眼,这也是我经常提醒我自己要警觉的一点。
刚才说,公诉人与刑庭法官有优势,但相较于我们律师而言,他们也有劣势。其主要的劣势有,一是工作量大,可能没我们律师那样有时间对一案子反复的研究,二是没有我们自由,我这里所说的自由,特别是指对案件作出独立判断、主张和决定的自由。也就是说,他们是专家,是精英,有些观点并非是他们不知道,只是决定他们取舍的因素与我们不同,受限因素比我们律师多。
第二个认同是,我们辩护工作,不是跟公安机关较劲,更不是跟公诉人、法官较劲,不是一定要与谁谁争个高下,不能意气用事、不必哗众取宠、一吐为快。用韩博士的话说,法庭上,争吵要不得,竞赛性辩护也要不得,所谓竞赛性辩护就是说会说,谁说得过谁,我们追求的应是有效性,注意辩护的有效性,法庭上,嗓门大口齿利,没有意见,有效才有意义。获得辩护有效性的重要路径是什么呢,我觉得主要应是“理性”、“客观”和“专业”。刑事律师要紧紧着力于当事人的利益,穷尽合法手段,力争其利益最大化。 我甚至觉得,我们辩护工作也谈不上维护法律与正义,我们的工作就是维护个案当事人的利益,在追逐这一目的的同时,达到司法设计中各角色的参与和制衡,从而使法律更合适的施用,最终起到维护法律与公义的作用。
第三个认同。体制的面目未必是体制内个体的个人面目。正常的情况下,案件承办人员对案件或案件当事人并不带有个人色彩,重判或轻判,他们无所谓。相对于辩护律师积极追求维护当事人利益的态度,司法人员更在意的是,把手头的工作快捷、稳妥的完成,别出漏子,不给自己挖坑、不为组织埋雷,案件对他们而言,就是工作而已。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应该是大多数体制内人士的态度。至于对被告人施以什么样的惩罚,只要在法律框架内,法律运用上有支撑、站的住脚,司法人员应不会计较的。因而,从这个方面看,律师与司法人员的冲突并不大,或者说不应该那么大,因为律师与司法人员追求的都是同一法律框架内的结果。
当然,我得说明,在任何一个阶段,任何一个环节,律师都要全力以赴、不留余力。我之所以说对公、检、法分用二五三不同的精力和关注,是打个比方,是说明我对一个刑事案件在不同诉讼阶段的关注度不同,是强调庭前辩护、诉讼过程性辩护的重要性。我从不敢坐等案件流程到审判程序,才去抖擞精神的“决战在法庭”,大多情况下,等案件到了法庭才着手辩护,黄花菜也凉了。
在侦查区块的二分力,请注意,我说的是在“侦查区块”,不是“侦查阶段”,在我的工作观念里,我以公检法的实质工作来划分,而不以普通的三阶段来划分,比如,侦查机关的工作,涉及逮捕前刑拘侦查、逮捕后羁押侦查、退侦期间补查,如果按“三阶段”来分,那么移送审核检查起诉前的阶段皆为侦查阶段,而我总是把侦查阶段中的报批捕工作,抽出来视为检查区块的工作。所以我用“侦查区块”、“检察区块”、“审判区块”这样的名称来表述。
当事人涉案初期最无助、最恐惧,也最容易被侦查机关把案情做实,有罪被做实倒也罢了,无罪或似是而非的情况下,因当事人在特定环境及情绪状态下的不当陈述而被做实,就会很被动。现实中这样的一种情况很多,被侦查员威逼、利诱而顺应侦查人员的意思做笔录的案例层出不穷。
2、要求当事人详细陈述在律师会见前已被讯问、问答、记载的内容。注意,是会见前“已被讯问、问答、记载的内容”,不是问当事人“案件事实”,即明确告诉当事人,律师现在不是问你事实是怎样的,是问你笔录的内容是怎样的。这是我经验技巧之一,大家也可用用,你自会悟到其中的妙处。要问细、问透,要让当事人多重复,要问到律师像看到讯问笔录一样,要问到律师对案情基本明白;
及时会见和第一次会见,很重要,万不可走过场,我一般至少用半天时间,需要时我会连续会见。前不久有个额度达数亿的诈骗案,我就连续四个工作日对其进行会见,直至我对案情了然于胸,得以形成理由充分的法律意见书呈送办案机关,办案机关听取了我的意见,当事人得以取保。当然,至于会见时如何与当事人完善委托手续、建立信任感、怎么样提高交流效率,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这里就不说了。
会见后就完事了吗?当然没有。我平时会在第一次会见结束后随即给当事人寄律师信。这封律师信,是我介入该案的第一份法律文书,题头为“律师通信函之侦查阶段律师信(一)”,只所以注写个(一),是因为我在侦查区块给当事人的律师信,往往不止一封。
关于给在押当事人写律师信的做法,我们上海分所的马朗律师做得比较好。与在押当事人通信,是律师的辩护权利,也是辩护方法。我本人从2012年开始到现在从始至终坚持运用这一工作方法。前段时间,杭州G20期间,会见询问当事人得知其没收到我早已经寄出的律师信,回去后我就给该看守所所长寄了封信,作以沟通和反映,很快就得到回复,解释是因G20抽调警力工作忙之故,律师信也很快就转交给了在押当事人。也就是说,律师信的方式是可行的,法律与实践中都没有障碍。我在侦查阶段律师信中,把会见过程简单回顾,说些宽慰安抚的话,把涉罪名的法条、解释、当时法院的具体适用性规定、程序性规定等材料内容,作为附件一并寄出。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在我们律师眼里很容易的法律,或许当事人搞不明白,或转身即忘,用纸质的材料寄给他,可附身携带,利于温习查阅,方便。打个比方,如果辩护律师像武林高手一样保护当事人不受司法机关围殴的话,不如教当事人一些招式,教会当事人与我们形成合力、一齐抵抗进攻。通过从介入案件到审判期间反复多次的对当事人的辅导,有时有些当事人就其个案的理解已有相当水准了,前段时间我有个当事人在法庭调查阶段侃侃而谈,条理清晰,表现抢眼,我暗自颇为得意,也乐见其成。这个案子尚没宣判,但因当事人的成功自辩,应会获得乐观结果。
我是通过第一次会见和第一封律师信来说明我的工作习惯,当然一个案子下来会有许多律师信,我列举一下我平时所写的类型:“律师通信函之 侦查阶段律师信(一)”,还可以有二有三之类的。根据不同的诉讼阶段和需要,还可以有《捕前律师信》、《逮捕后律师信》 、《移送起诉律师信》、《庭前律师信》、《庭后律师信》、《判后律师信》等等。这些信件一列出来,显得很多,实际分散在动辄半年一年的诉讼过程中并不多。
律师信的名称可自由拟定,内容亦可据需而文。可以是确为案件所需而发信,像刚才我所说第一次会见后的律师信,很重要。也可以是侧重告知程序作用的信,比如《庭前告知信》,虽然在庭前会见时已经讲过相应内容,我仍会把开庭的需要注意的几点及程序以书面形式寄给当事人,让当事人庭前多看看,做到心里有数,在庭上表现的更好些。还可以是起礼节上收尾作用的信,为工作结束来个完美的句号,如《判后律师信》。比如前几天,我对一个当事人进行了宣判后会见,回来后就给他寄了封律师信,安慰安慰,祝福祝福,表达了我通过案件的阴差阳错认识了他,对其人格魅力印象非常深刻,等等。赠人玫瑰手留余香。一封信,对我们自由之身而言,举手之劳而已,却温暖了他人,宣传了大成刑事律师规范专业上档次,当然也宣传了自己,何乐不为呢?
强制措施方面的工作,主要是《不予批捕法律意见》及《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的提出,分为提请逮捕阶段的《不予批捕法律意见书》、逮捕后移送审核检查起诉前的《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审查起诉阶段的《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
第一,提请逮捕阶段。这七天,在我眼里,是刑事案件中最为黄金的七天。相对于公安人员,检察人员的法律素养高出一些,如果认为律师与警察交流,是秀才遇到兵,那么律师与检察员交流则是秀才遇秀才。当然这是开玩笑,大部分公安人员也是挺优秀的。我是说,要重视这一环节,也要相信承办人大多不会无端不听取你的建议。
我们知道,此时案件与检察机关(是指公安报捕的案件)没什么利害关系,在对当事人逮捕之前,检察机关对案件的对错、定性、质量等不承担相应的责任,案件结果对检察机关形不成掣肘,而在逮捕之后,对案件的处理,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就成了系在一条绳子上的蚂蚱,成了利益共同体。
我有时是在向侦查机关提交《取保候审申请》的同时,也拟好了《不予批捕意见书》,一则我对公安机关对当事人不予取保做足了心理上的准备,二则报批捕期仅七天,还必然包含周六周日两个休息日,还应该要考虑承办人提审时间安排,还需要注意到侦查机关提交报捕的时间你很难第一时间掌握。总之,我多是准备好《不予批捕意见书》,瞪着双眼,一旦查悉到是哪个检察员承办,立即联系,双手奉上书面材料。
这是检察区块最重要的工作内容。我认为这也是像报捕阶段一样重要的黄金期。刚才说过,在逮捕之后,对案件的处理,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公安与检察机关就成了系在一条绳子上的蚂蚱,成了利益共同体。但在不改变罪与非罪的前提下,也就是在不对抗检察机关对当事人逮捕正当性的前提下,如何起诉,起诉与不起诉,起诉多少,起诉什么罪名,检察机关有极大的选择空间。这一段时期,检察机关的比审判机关还具审判权,直接取舍案件的生死,甚至不受实质性监督。
我平时所做就是把我的阅卷笔录作为我的法律意见书附件呈送给办案人员,大多数都是装订好,有封皮,有目录,阅卷笔录要详细,要按不同的标准,从不同角度,结合起诉意见书中分节事实进行摘取、归纳、列表等,而不是简单的几张纸。
吃透案件,要有清晰的辩护思路,这一点很重要,是前提,但思路清晰并不代表书面观点的唯一。如我有一个诈骗案,在审核检查起诉阶段,在递交的不起诉意见书中,我提出了三个不同辩护观点,公诉人问我怎么有不同观点,到底辩点是哪个,我说案子在审核检查起诉,应该说公诉观点还没最终形成,所以我们的辩护观点也没法确定,我说我这里提交的几个观点,是我对这个案子的理解,提供给你们审核检查起诉时做参考,看哪一个更符合你们的判断。当然,这三种观点都是指向不起诉的。后来,这个案子检察院建议公安机关撤案了。
意见要中肯,客观,不能自说自话,要做到三个理解,理解案情、理解法律、理解操作,不能以个人单一视角只顾一说了之。大成北京刑事部主任赵运恒律师提出过一个“大辩护”概念,啥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刑事律师在办案中要了解背影、知悉形势,要看操作性,要有大的格局观!
总之,在当前的司法环境条件下,就普通的刑事案件而言,案件的诉讼程序越靠后,解决的难度越大,而其中在审核检查起诉阶段,是极为出辩护成果的时候。记住,在公诉书形成之前,或者再往前推,在公诉人尚未形成案件观点前,公诉人与律师基本不存在对抗,此时可完全进行业务上坦诚的交流,估计没有哪个公诉人不欢迎律师及早的提出法律意见。你想,只要律师说得有道理,公诉人在起诉时采纳律师意见就是,查了漏补了缺少了对抗,案子办的既稳妥又漂亮,皆大欢喜。真正的对抗在公诉书出来后,才形成。
前几日的大成三亚刑事论坛上,帅气优秀的公诉人陈锐说,“在公诉书出来前,公诉人是最有权威也是最公正的裁判者”,这话对我们刑事律师有很好的启示。关于这一点,记得在大成刑辩学院第一期的互动交流环节,我们大成上海的同事朱海滨律师也提到了这一观点。
我这里所说的庭前提前辩护,其实是指开庭前向法庭提交初步辩护提纲式意见,让法官知道律师的观点是什么,争议焦点在哪里。这样做的好处是,这会使法庭更准确高效的把握庭审,法官乐于接受,当然在庭审中会关注到律师想让法庭关注到的东西。
具体如何与法官联系,今天的主持人王勇大律师有独到见解,其在三亚大成刑事宣讲中,专门就“一审阶段如何与法官有效沟通”这一主题,进行了很棒的解读,详实细腻,相当实用,可完全作为我们在审判阶段与法官沟通的操作指引,显然是王律师将其实践经验结晶进行了无私的奉献,这里也给王勇大律师点个赞。同事们可向其索取文字稿,用来学习。
在庭前提交辩护意见时,若案件复杂,材料多信息大些,如同在审核检查起诉阶段一样,我会将详细的阅卷笔录及证据分类作为附件与辩护意见装订在一起,一般是装订为带有前后封皮的很正规的那种,进行提交。同样注意及时性,尽量在法官阅卷前提交,以便于先入为主,影响审判者。
关于当庭的辩护,我平时的做法是,注重每一个审庭过程,万不可以为重头戏仅仅在辩论阶段。你认为法庭辩护最重要,法官可不一定这么认为。如果你留意,是不是会发现,很多时候,审判长宣布“法庭调查结束,下面开始法庭辩论”后,常常习惯于身体向后一仰,靠在靠背椅上,一脸的轻松。你认为大戏开始的时候,审判者内心里真正的工作已结束了,听或不听,“控辩双方观点已记录在案,庭后合议”就是了。所以,我们刑事律师一定要重视辩论前环节,因为辩论前阶段特别是法庭调查环节,法官最重视。陈锐先生又说,“法庭上,公诉人与辩护人各有五轮对应的表达机会,包括对起诉书的观点、对当事人的问询、对证据的质证、辩护意见的阐述及辨论观点的展开,每一轮都不应该浪费。”说得很有道理,当时的与会者一致认为受到启发,详细的细节内容,同事们可留意刑事部整理的文字稿,的确值得学习。
关于辩护意见的发表,同事们近几日应多已拜读过许昔龙大律师谈“辩护意见的发表”的文章。其在文章中谈到,辩护意见的表达要脱稿而不离稿,禁忌低头念稿,法庭辩论不必过多的客套,宜直接表明观点,摆明立场,不以取悦旁听人为目标,遵守规则、照顾全局等等。说的很好,我极为认同。我平时发表辩护意见的时候都是脱稿的,反倒是一旦看稿反而说得不流畅了,不会说了,这样也不好。由于之前已倾注大量精力,所以案件在进入审判阶段时,我对案件已经相当熟悉,何况庭也提交有法律意见,故而在法庭上能很好把控全局,据庭审实际调整应对方式,辩论时,更是紧贴庭审,辩护意见的主线下临场陈词。当庭辩词的技巧和渲染可以有,但不重要,发表辩词的要点在于让法官听得明白,听得进去。
当庭辩护,还涉及到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当庭的发问。关于当庭发问的技术,大成太原刑事部主任马俊,有一专题讲座,题目是《庭审发问阶段的技术探讨》,讲得很好,其中设置分组发问题目的做法,我就很受教。本周四的庭上我便学以致用,比如我对当事人说“下面我问人第一组问题,这组问题是关于你所在公司成立、股东变更及不同时期的责任人方面的”,这么一问大家都听的明白,当事人也知道我要的答案,公诉人也不好说律师诱导和预设答案,实际效果还不错,所以也借这个机会,谢谢马俊律师这位青年才俊,大家也可向他索要文字稿学习。
开过庭,当然不是工作的结束。我的正式辩护词多是在庭后提交法庭的,是结合庭前提交的辩护提纲或意见、开庭的新情况、开过庭后的新思考,出具份完善的正式的书面辩护意见。这份意见提交后,仍可据需要随时提交新的书面辩护意见。虽然合议庭经常说,新的辩护意见没有在法庭上呈现和辩论,不会表述在判决书中,但我们不必在意,不要因此就不提交,合议庭不表述在判决书中不等于不注意到你的意见,不等于该意见对其不产生一定的影响。何况,我们当庭的辩护意见,又有多少写进了判决文书了呢。
一是庭后若有有利证据,仍要提交,不要受制于提交时间、是否原件等证据规则,发现就提,没有原件,复制件也提。刑事证据的合法性规则主要是约束司法机关、约束公权力的,当事人及我们辩护人提出材料、意见即可。刑事与民事不同,刑事就是要查清案情嘛。关于这一点,刘广三教授亦有过简明入理的释述。当然,有条件遵循合法性规则的更好。
二是,根据案件情况,庭后可为当事人提出变更强制措施的申请。这种申请或许没有被法院同意的结果,但也不排除先行取保的可能,再者,这种申请没坏处,有时甚至审判人员不排斥律师这样做,特定的案情下,这种申请会成为合议庭向领导反映案情和与公诉机关沟通案情的重要材料,可为一用。
说到这里,总结一下,我所说的“253辩护”,无非是把我个人的办案过程向大家汇报一下。当然,这是一个假定的流程,我们有时可能是只介入案件的一个阶段,但无论如何,我们树立过程性辩护的工作理念是很有必要的。
我刚才还就我今天的发言和想法,列出了十句线、要理解我们的公检法体系,理解我们的司法环境和实际,要认识到一线司法人员的专业、辛苦和不自由,一般别急于把他们视为律师的敌对方,他们不是,也没有必要。